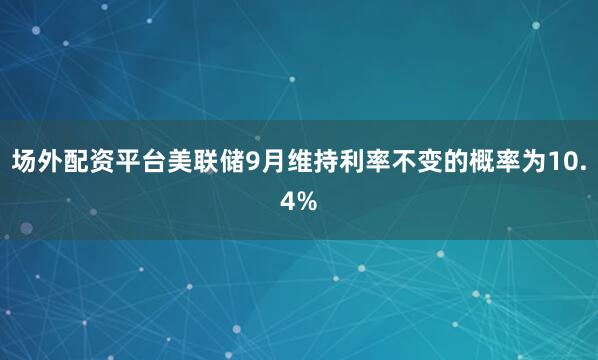《明季滇黔佛教考序》
文/陈寅恪
意译/梅明(纪录片《陈垣》导演)
中国的史学成就以宋朝为盛,但宋史对于宗教的记载很简略。不仅源于观念的偏见,也是因为睁眼看世界不够多。到了元、明、清三代,更趋微渺。所以在中国历史著作之中,几乎没有一部完善的宗教史。近代以来新辟中国宗教史,是从江门陈垣(援庵)先生的著作开始的。
陈垣先生著摩尼教、佛教诸文,海内外学者都读并仰慕着。今战火纷飞,千里之外,先生托书,深嘱为序。我甚爱佛学经典,又旅居云南,然对书中所引用的资料,未见者十之七八。先生搜罗材料的勤勉,见闻的广博,世所罕见。至于见解判断的精辟,体例结构的完善,一以贯之,无需多言。
展开剩余82%读完书后,我掩卷而思。世上有人认为宗教和政治是两回事,不能放在一起讨论。但史实表明,宗教与政治不可能完全没有关系。就拿本书来说,南明永历年间,云南、贵州是当时的京畿要地,华夏正统所在的地方。在那个艰难危险的年代,边疆一隅之地,还能勉强汇集起中华文化的精英人物,原因就在于此。等到南明灭亡,那里的学者和正直之士,相继逃入佛门以保全气节。以古思今,这本被称为宗教史的书,未尝不能当作政治史来读。
悲哉!遥想西晋永嘉之乱时,僧人支愍度准备渡江避难,与一位落魄的道人结伴同行。他俩商量:“如果还用原来的教义去江东,恐怕会没饭吃。”于是两人就共同创立了“心无义”的学说。后来道人没有渡江,而支愍度在江东宣讲“心无义”学说多年。过了许久,道人托人带话给支愍度说:“哪有什么‘心无义’?不过是权宜之计解决饭碗罢了。千万不要因此辜负了佛祖如来!”
回望1937年秋,我在北平痛别先生,等到达长沙时,南京惨遭沦陷。不得已我向南逃往瘴气弥漫的广西,又辗转迁徙于云南的滇池、洱海,也将近三年了。这三年中,天下大变,变节做汉奸者,触目惊心。先生在沦陷区北平延续国学,借辅仁大学教会学校的身份坚持抗日,苦苦支撑;而我则在西南大后方的广阔天地间奔波谋生,坚持在西南联大授课,庚续文脉。
我们南北相隔,同观山河破碎,想必都是断骨锥心之痛。所幸我与先生研习国史大半辈子,弘扬中华文化之心至死不渝。值此危难之际,先生还有国史新著问世,弟欢呼雀跃,先生对得起列祖列宗。
现在先生大作即将刊印完毕,我却不能伴在北平、做些校对的辅助工作,只能从万里之外遥寄一篇序言,以飨读者。这些灾难究竟是谁造成的?又是谁导致的呢?这难道不正是宗教与政治虽然不同,但终究不能完全无关的一个明证吗?
1940年岁次庚辰七月陈寅恪谨序
译者手记(梅明):
“史学二陈”的故事很传奇,也很难懂。我之所以选择意译,就是希望翻译自由度大一些,尽量能让中小学生都能看懂,以便于传播励耘精神和二陈的学术思想。
钱穆说陈寅恪氏论文:“冗沓而多枝节……且多临深为高,故作摇曳。”这是用文学的标准看史学。就史学而言,“冗沓而多枝节”是优点,也就是详尽而全面深入。
这篇序的翻译用什么标准呢?
一是文学标准,简约生动,如身临其境。
二是传播学标准,因信件寄往沦陷区,寅恪先生担心因言致祸,所以言之未尽。如果直译,缺失了很多历史背景,又有很多半截话,观众难以理解。所以我补上了历史背景,把未尽之言也写全了。
肯定会有不妥之处,二位先师见谅。
附:明季滇黔佛教考序
中国史学莫盛于宋,而宋代史学之著述,于宗教往往疏略,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,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。元明及清,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,故严格言之,中国乙部之中,几无完善之宗教史。然其有之,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。
先生先后考释摩尼佛教诸文,海内外学者咸已诵读而仰慕之矣。今复以所著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远寄寅恪读之,并命缀以一言。寅恪颇喜读内典,又旅居滇地,而于先生是书徵引之资料,所未见者,殆十之七八。其搜罗之勤,闻见之博若是。至识断之精,体制之善,亦同先生前此考释宗教诸文,是又读是书者所共知,无待赘言者也。
抑寅恪读是书竟,别有感焉。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,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。然自来史实所昭示,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。即就先生是书所述者言之,明末永历之世,滇黔实当日之畿辅,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。故值艰危扰攘之际,以边徼一隅之地,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,盖由于此。及明社既屋,其地之学人端士,相率遁逃于禅,以全其志节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,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,虽曰宗教史,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。
呜呼!昔晋永嘉之乱,支愍度始欲过江,与一伧道人为侣。谋曰:“用旧义往江东,恐不办得食。”便共立心无义。既而此道人不成渡,愍度果讲义积年。后此道人寄语愍度云:“心无义那可立,治此计,权救饥耳。无为遂负如来也!”忆丁丑之秋,寅恪别先生于燕京,及抵长沙,而金陵瓦解。乃南驰苍梧瘴海,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,亦将三岁矣。此三岁中,天下之变无穷。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,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,南北相望,幸俱未树新义,以负如来。
今先生是书刊印将毕,寅恪不获躬执校雠之役于景山北海之旁,仅远自万里海山之外,寄以序言,藉告并世之喜读是书者。谁实为之,孰令致之,岂非宗教与政治虽不同物,而终不能无所关涉之一例证欤?
一九四〇年岁次庚辰七月陈寅恪谨序。
中山大学摄影 纪录片《陈垣》摄制组
发布于:北京市优配网,配资实力股票配资门户,天创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